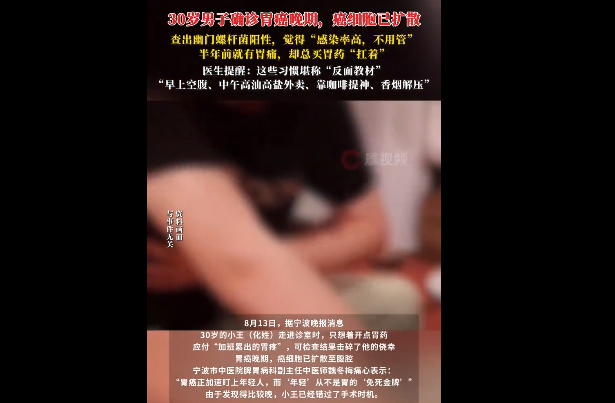今年是60年一遇热夏?看看农谚怎么说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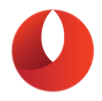 摘要:
四月的暖风刚吹透庄稼地头,老辈人总爱蹲在田埂上念叨:"这天气热不热,还得看四月十五的讲究"。今早天刚蒙蒙亮,王哥就披着单褂站在晒谷场,盯着东南角刚冒头的日头直咂嘴,手里攥着的铜烟锅...
摘要:
四月的暖风刚吹透庄稼地头,老辈人总爱蹲在田埂上念叨:"这天气热不热,还得看四月十五的讲究"。今早天刚蒙蒙亮,王哥就披着单褂站在晒谷场,盯着东南角刚冒头的日头直咂嘴,手里攥着的铜烟锅... 四月的暖风刚吹透庄稼地头,老辈人总爱蹲在田埂上念叨:"这天气热不热,还得看四月十五的讲究"。今早天刚蒙蒙亮,王哥就披着单褂站在晒谷场,盯着东南角刚冒头的日头直咂嘴,手里攥着的铜烟锅在青石板上磕出清脆的响。
农谚里藏着千年智慧,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。庄稼把式都知道,四月半的天气就像个调皮的娃娃,早晨露水重得像撒了层盐,晌午日头毒得能晒蔫瓜苗,这样的天气变化最会透底细。要是这天日头升得急,云彩薄得透亮,连草叶尖上的露珠都存不住半个时辰,老辈人准会拍着大腿说:"今年这暑气要成精"。
晌午时分,灶屋烟囱冒出的炊烟直往上蹿,连个弯都不带拐。李婶子端着簸箕站在屋檐下,看着自家院里那棵老槐树直嘀咕:"怪事了,往年这时候树影子早该爬到水井沿了,今儿个树叶子蔫蔫的,影子缩得跟个团似的"。这话可不假,庄稼人看天象的功夫都在这些细枝末节里,树影子的长短比温度计还准成。
日头偏西那会儿,村头池塘里的蛤蟆叫得比往常早半个时辰。张大爷拎着竹篓往家走,听见这动静突然站住脚,扭头对后生们说:"早些年碰上这光景,我爷爷那辈人早把蓑衣斗笠备下了"。要论看天气,水里游的比天上飞的更灵光,蛤蟆提前开嗓,十有八九是憋着场大热天。
村西头的老榆树底下聚着七八个老汉。赵老爷子拿烟袋杆指着树梢上新结的榆钱:"瞅见没?这榆钱子比去年厚实三成不止"。这话引得众人直点头——榆钱长得密实,树冠沉甸甸地往下压,正是老辈人说的"天热催物长"的征兆。
夜风裹着燥热在村子里打转,连看家狗都趴在门槛上吐舌头。刘家媳妇收拾完碗筷,站在院里晾衣裳,摸着竹竿上晒得发烫的粗布衣裳直犯愁:"这才四月半,晾衣裳两个时辰就干透,往常年这时候得晾到日头落山呢"。要论过日子的小窍门,庄稼户的媳妇们个个都是气象行家,衣裳干得快慢就是最灵验的温度计。
月亮爬过房梁时,村东头的麦子地沙沙作响。守夜的孙老汉提着马灯在地头转悠,灯影里麦穗齐刷刷往东南方向歪。他蹲下身捻了把土,土坷垃在手里碎成粉末:"这地气干得透透的,跟烤过的面饼似的"。老庄稼把式都懂,四月半的土性子最藏不住秘密,干土热风碰上润土凉气,准要闹出大动静。